智能時代背景下的戰爭思考 ——讀《智能化戰爭論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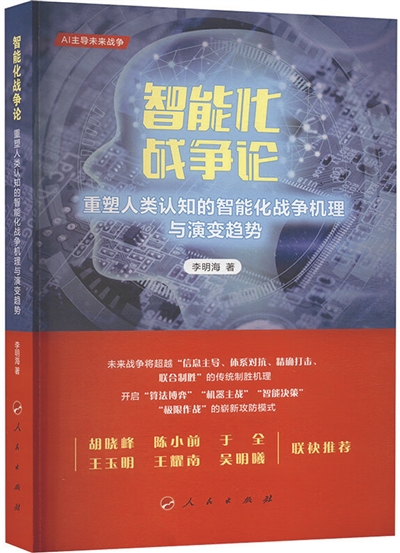
戰爭歷史證明,科學技術的發明,往往首先應用于軍事領域。隨著信息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,及其在軍事領域的廣泛應用,促使戰爭形態加速從信息化向智能化演變。這種演變對制勝機理帶來的影響,已成為軍事理論界的研究熱點。
國防大學教授李明海在長期跟蹤研究戰爭理論、戰爭實踐和戰爭形態演變等問題的基礎上,深入思考、分析研究,緊緊圍繞如何認識、怎樣打贏未來智能化戰爭,推出《智能化戰爭論》(人民出版社)。
《智能化戰爭論》中的研究成果,與現代局部戰爭實踐具有一定的交互與契合。該書闡述的信息化戰爭向智能化戰爭發展的“四大轉變”:即對抗方式從“體系對抗”向“算法博弈”轉變、作戰要素從“信息主導”向“機器主戰”轉變、決策方式從“人腦決策”向“智能決策”轉變、作戰樣式從“斷鏈破體”向“極限作戰”轉變,揭示的“算法優勢主導戰爭優勢”“機器主戰重塑作戰流程”“智能決策優化作戰行動”“極限作戰顛覆作戰樣式”等智能化戰爭制勝機理,構設的無人化作戰等10類智能化戰爭的典型作戰場景等,在近期世界不同地域發生的戰爭實踐中,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和印證。這充分說明《智能化戰爭論》的實踐基礎和理論前瞻特征。
《智能化戰爭論》的基本思想,立足于打贏混合博弈智能化局部戰爭。當前,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,大國博弈突破傳統地緣政治邊界,向科技制高點爭奪、規則體系較量、認知域滲透等多維度延展,呈現出軍事對抗與非軍事施壓、實體摧毀與虛擬控制交織的混合博弈復雜景象。《智能化戰爭論》突破傳統軍事理論經驗歸納、對策研究的思維方式,對智能化戰爭10個維度的解構,既植根于馬克思主義戰爭觀和方法論的沃土,又融合量子計算、腦機接口等前沿科技認知。這種將“硅基智慧”與“碳基思維”融合的理論探索,體現了新時代我軍軍事理論創新的價值追求。
《智能化戰爭論》中談到的AI技術和武器裝備,與當今世界AI發展浪潮密切耦合連接。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展不斷刷新人們對軍事問題的認知,戰爭理論研究也迎來了大革新、大爆發、大突破的新機遇。《智能化戰爭論》敏銳捕捉到“技術奇點”臨近的征兆,從戰爭形態深刻演變的歷史進程與人工智能技術發展進步的現狀,由淺入深對智能化戰爭理論進行系統研究和分析。書中論述的技術迭代將引發“混合博弈”升級,軍事競爭不再局限于武器平臺對抗,而是向物理域、信息域、認知域等全域延伸;當無人集群自主協同、智能體戰場自組織、深度偽造認知攻防等技術突破軍事應用的“摩爾臨界點”,戰爭形態必將經歷從“信息化賦能”到“智能化重構”的變革,這種必然性根植于技術演進與社會形態的雙重變革;智能化戰爭“技術即戰術、算法即兵法”的本質特點;大國博弈從“制陸權”、“制海權”向“制智權”躍遷;技術優勢將成為國家安全的戰略支點等理論觀點,讀后使人感到耳目一新。
《智能化戰爭論》中的智能時代作戰理念,繼承我國優秀傳統兵法精髓。《智能化戰爭論》展現出東方軍事智慧的穿透力,開篇即追溯中國兩千多年前《孫子兵法》的“上兵伐謀”思想,將“不戰而屈人之兵”的謀略內核注入智能化戰爭場景。書中論述的,智能化戰爭的自主性、全域性、涌現性、迭代性等特征,既繼承了《孫子兵法》“奇正相生”的辯證思想,又融入了復雜系統科學的“自組織”原理。同時,《智能化戰爭論》還參考借鑒克勞塞維茨《戰爭論》中的“戰爭迷霧”理論觀點,提出“數據迷霧”等新的概念。這種“古為今用,洋為中用”的理論思維方式和創新方法,使智能化戰爭研究跨越了時空界限、超越了技術層面的探討。
從以上意義上講,《智能化戰爭論》是對未來戰爭的有益探索,對我們學習、認識、研究智能化戰爭具有啟示意義。盡管如此,不能不說,智能化戰爭是明天的戰爭,是初見端倪的未來戰爭形態。受技術發展和戰爭實踐等多種因素的制約,目前我們對這種戰爭形態的認識還是初步的,理論成果也需要在未來戰爭實踐中接受檢驗。
科學技術不斷進步,戰爭實踐不斷發展,人們對戰爭的認識將不斷深化,軍事理論也將不斷創新。期待廣大軍事理論研究者,以及熱心關注智能化戰爭的人們,推出更多更好的理論創新成果,為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現代軍事理論作出更多貢獻。